打开微信,扫一扫二维码
订阅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打开手机,扫一扫二维码
即可通过手机访问网站并分享给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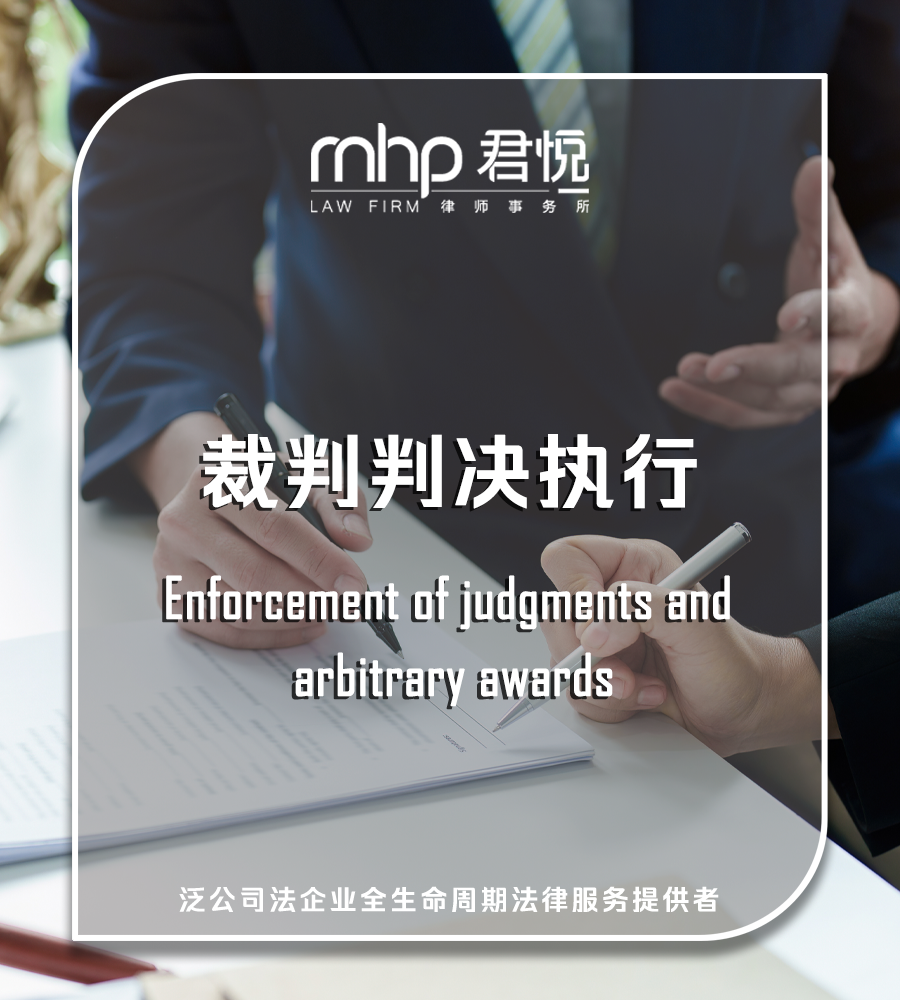
2024年6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提出过一个法发[2024]9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交叉执行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该《意见》分为一、总体要求;二、关于督促执行、指令执行和提级执行;三、关于集中执行;四、关于协同执行和执行协调;五、关于监督管理;六、附则等六部分共计28条。从上海法院发布的信息来看,上海法院应该已经在落实这个指导意见,但具体是否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化的执行工作尚不得而知。最高法院在《意见》的开头提出了实施《意见》的目的性,即“为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监督管理,推进交叉执行工作法治化、规范化、常态化运行,加快实现切实解决执行难目标。”相信最高法院印发这个《通知》应该是看到了消极执行、选择性执行、规避抗拒执行、非法干预执行、阻碍执行等顽疾屡治不愈,地方保护主义和地域性的执行阻力依然存在等问题,从而提升交叉执行的要求和监督,以求加快切实解决执行难的步伐。对此,笔者深表赞同。但是,任何一个机制的落实都无法避开实践性问题,也即落实效果在执行实践中的反映。笔者以为,《意见》如果想要常态化地运行下去,会面临几个问题需要解决。笔者在此谈几点粗浅的看法。
便利性原则缺乏具体地域管辖的标准
《意见》第2条提到人民法院开展交叉执行应当参照我国民事诉讼程序关于地域管辖的“两便原则”精神,统筹考虑当事人住所地、主要财产所在地、执行法院案件数量、执行力量等因素,从便于当事人参与执行、便于人民法院依法及时有效开展执行工作出发,合理确定交叉执行案件和交叉执行法院。这样一个原则性规定体现了最高法院对交叉执行管辖问题的一个总体考虑,但是从实践角度出发,仍然缺乏一个交叉执行管辖的具体标准。在全国法院执行条线案多人少矛盾突出的前提下,这个问题可能会被无限放大,最终会体现在各地高院结合自身情况制定的相关实施细则中。如此,将极易产生因执行标准不统一而导致同类案件各地法院对交叉执行管辖标准不同,执行结果也不同的现象。《意见》的第六部分附则中,尽管最高法院提出了各高级法院制定辖区关于交叉执行的实施细则报最高法院审查备案的要求,但是笔者感觉,从避免乱执行及执行推诿角度以及统一全国执行标准、利于案件协调出发,最高法院应出台一个全国性的《交叉执行管辖的实施细则》为妥,尤其是统一交叉执行案的管辖与立案标准。就交叉执行来说,管辖就是个门槛,这个门槛的高低要求不统一,交叉执行的结果将很难令人满意,也会带来各级法院因此导致的立案问题,同时也将会对法院的数据准确性带来一定的冲击。
督促执行、指令执行和提级执行的情形要求与现实执行状况脱节
《意见》第4条规定了符合督促执行、指令执行和提级执行的几种情况,包括存在消极执行、拖延执行问题;案件受到非法干预;案件重大疑难复杂等。其中关于存在消极执行和拖延执行的标准为“对申请执行人提供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或者执行过程中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执行法院自执行立案之日起超过六个月对该财产未执行完结的;对于行为执行的,执行法院自执行案件立案之日起超过六个月未采取相应执行措施的。”从执行实践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普通的执行案件,只要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并且涉案财产需要通过执行处置程序(比如评估、拍卖等)来变现的,那么即使被执行人或利害关系人未设置任何障碍,执行法官从执行案件立案之日起走完整个执行程序,直至发还相关处置款项,一般在六个月内很难实现执行完结的目标。当然,简单的划拨银行存款、强制抛售有价证券、提取被执行人收入等不在此列。所以,现实中那么多有财产可供执行的终本案件的产生就是因为法院执行系统结案标准和结案时间的考核要求与执行现状脱节造成的后果,导致大量有财产可供执行的案件躺在终本的水池里无人问津,对申请执行人来说恢复执行实为艰辛。笔者记得前几年最高法院曾经要求各级人民法院清理终本案件中有财产可供执行的案件,但最后因为在新收执行案件年年增量的情况下这类案件数量实在过于庞大,超出了法院现有的承载能力而变得无疾而终。相信最高法院最初的目的是为了解决消极执行、拖延执行的顽症,但忽视了一个现实,大部分超过六个月未执行完结财产的案件并非源自法官的消极或拖延,而是力所不能及。当听说不少基层法院对执行法官月结案数考核要求已经达到30件时,执行考核要求与《意见》的要求已经产生极大的冲突,笔者觉得《意见》对督促执行、指令执行和提级执行设置的门槛过于简单粗暴,因此在《意见》已确定情形的基础上设立详细的甄别细则才能有助于在执行实践中去落实《意见》的精神,仅有框架是很难将《意见》真正落实到执行实践中取得。同时,呼吁了多年的执行考核改革,如果能落实到实处,会是对《意见》有效落实的最大利好。
再次指令的规定对提级执行可能产生反向效果
《意见》第10条提出,指令一般以两次为限,经过两次指令执行后,上级法院认为仍有必要继续交叉执行的,一般应提级执行。这一条涉及到了上下级法院之间的监督和管理问题,但是没有对执行法院在指定期间内无正当理由未执行完结或者受指令法院在法定执行期限内无正当理由未执行完结的赋予真正意义上的责任规则。当提级执行成为兜底时,试想一下上级法院将会面临怎样的困境?最高法院的初衷是好的,希望通过交叉执行来破解部分消极执行和执行干预的问题,但是既然上级法院做出了督促执行或者指令执行的决定,那么就意味着原执行法院或者前任执行法院存在着主观上的执行过错,在经过上级法院督促执行或指令执行后仍未整改,提级执行固然是一种解决途径,却不是最优解,尤其是经过两次指令执行仍无正当理由未及时执行完结的。笔者以为,如何尽可能避免提级执行的发生,应该是后续实践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否则会与《意见》的本意出现反向的效果。
集中执行的利好
过往的执行实践中,常常会遇到一种奇怪的现象,当一个被执行人的财产被一家法院执行查控或者不同类别的财产被不同法院执行查控,在其面临多个债权人,且案件分别有多家法院受理执行时,所有案件的执行都会出现一种较为统一的停滞不前,理由包括首封案执行标的远小于不可分割财产的价值、各法院分别执行的案件存在优先债权与普通债权的交集导致财产分配差异、执行措施的先后顺位及覆盖范围的交叉等。因各执行法院无法统一执行标准而导致案件整体推进不利,从而对债权人也即申请执行人造成极大损害。《意见》发布之前,这种情况通常只有由相关法院的上级法院进行协调后统一将案件移送某一家法院执行,但这种协调大多都是被动的,往往源于当事人的信访,甚至有时上级法院还要涉及异地法院,协调起来不甚顺畅。《意见》第三部分第12-16条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一点笔者深感欣慰。但是上级法院如何决定启动集中执行,或者什么条件下上级法院可以决定启动集中执行,《意见》中尚未得到完整的体现,希望在后续的实践中能得到进一步的细化。
交叉执行其实只是人民法院的一种自我的查缺补漏措施,在当下的执行实践中的确能解决某些问题,但这只应成为过渡性的措施,《意见》也只是对这种措施的规范,希望有一天交叉执行会退出历史舞台,那么如今这个《意见》的公布与施行才会变得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