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微信,扫一扫二维码
订阅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打开手机,扫一扫二维码
即可通过手机访问网站并分享给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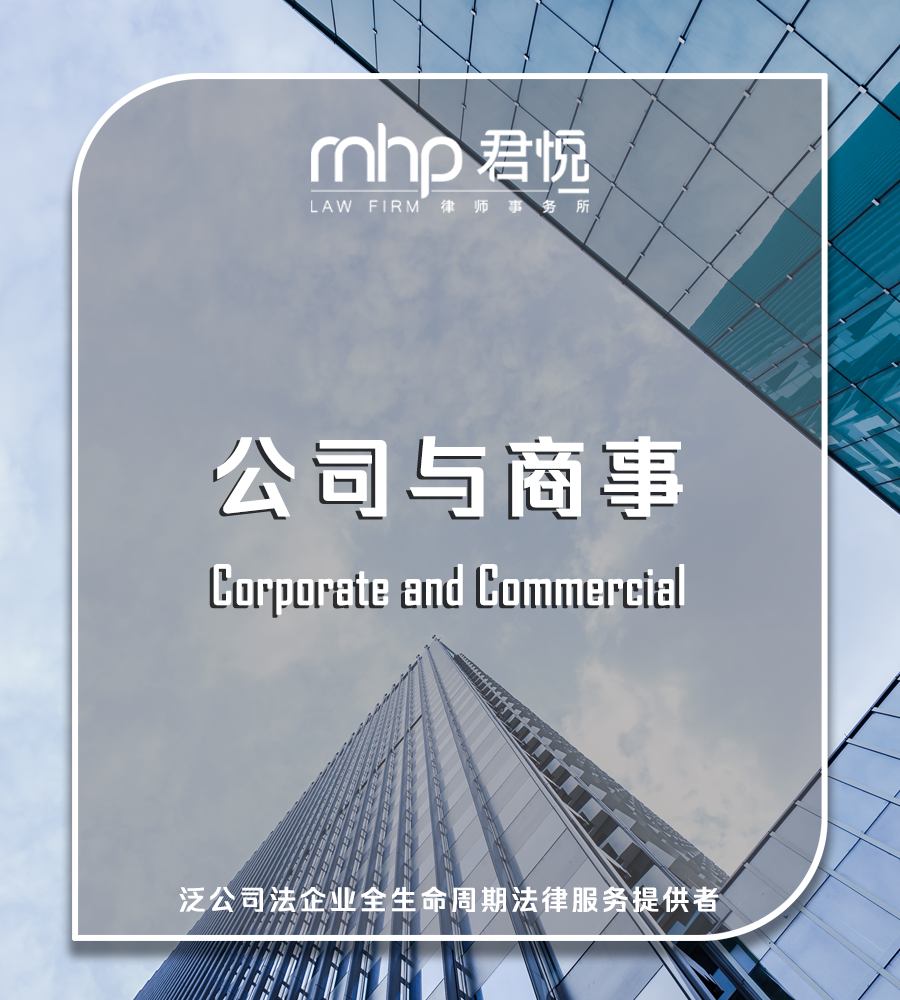
前言
商事争议解决中,管辖权争议对于攻防双方来说,都是必要且不可或缺的博弈维度。一方面,管辖权攻防涉及潜在裁判机关的变化,从而带来裁判口径、保全难度、举证策略三点变化,使得双方的诉讼策略和争议优势地位相继发生变化。另一方面,管辖权异议作为独立的争议前置程序,其也给需要拖延时间的一方,带来了以时间换取空间的机会。在种种管辖权争议的形态中,围绕公司住所地认定来发起争议,是异议方所常见的策略。 此种情况下,在商业实践中普遍存在公司注册地与经营地不一致的情形时,如何识别公司住所地从而确定管辖成为了司法实践中的一项难题。作为全国主要经济核心城市之一的上海,司法机关对此的实践无疑具有较强地指导和借鉴价值。 1、由公司住所地管辖的立法本意 《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而对于如何认定住所地,现实中存在难点,其原因如上文所述,公司注册地与实际经营地不一致在现实中已成为普遍情形,尽管《民法典》第六十三条中明确要求法人应将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登记为住所,但实践中往往经营者另有商业诉求而不能遵守,加之大量历史遗留问题需要解决,故这一“两地冲突”现象在现阶段仍未得到较大改善。 正是基于这一现状,《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三条明确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住所地为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只有在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不能确定时,才以注册地为住所地。换言之,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应优先于注册地作为厘定相应管辖的首要标准。 此种解释背后的立法逻辑在于,对涉公司纠纷,公司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就争议往往有更为密切的联系,该所在地法院通常更适合处理有关争议。只有当公司存在至少两个以上的办事机构,致使当事方对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的认定存在争议时,因进一步明确辨别主要办事机构的标准难以统一,故以公司注册地确定为住所地为宜。 2、对公司住所地的查明路径 首轮核查 首轮核查发生于案件立案的过程,期间的举证责任分配受到法律规定和法院立案程序的共同影响,在本地司法体系中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实践。 尽管根据法律规定,对公司住所地的判断首先需要确定是否存在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即提起诉讼一方需证明被告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受到立案的法院管辖,法院才能有所依的受理立案申请。 然而,实践中为减轻当事人的立案负担,且考虑起诉方的单方举证无法构成判断公司住所地的稳定考量基础,司法实践中通常倾向于起诉方证明公司注册地即视为满足立案条件。 次轮核查 法院受理案件后,如相对方提出管辖异议,则举证责任的分配将发生转化。此时,初步举证责任将从原告转移到被告,从原告证明法院有管辖权,即公司住所地在该法院所在地;转化为被告证明法院没有管辖权,即该法院所在地并非公司住所地。 三轮举证(或有) 笔者认为,就立法本意而言,双方在对公司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进行举证后,双方还有可能就另一事实问题,即公司是否有多个办公机构进行举证。其原因在于,依照法律规定如公司在至少两个及以上的地址经营,包括其实际办公地点、生产经营地、销售地点等等,而难以确定哪一个地址属于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此时方可回归以公司注册地确定为住所地以确定管辖。 3、通常证明公司住所地的举证途径 从全国司法实践来看,欲举证公司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从而据以确定管辖,实践中常见的有以下证据: 1. 与该公司之间的合同 2. 该公司办公场所现场照片 3. 与该公司往来函件的快递底单 4. 该公司人员的名片 5. 与该公司人员在其办公场所会面的会议通知 6. 该公司企业年报登记的联系地址 7. 该公司官网、微信公众号公布的联系方式 8. 该公司官网、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搬迁信息、在其办公场所举办活动的宣传文章 9. 该公司在其他案件中披露的联系地址 此外,还可以提供该公司注册地现场照片,以证明该公司注册地与实际经营地不一致,其注册地并非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 4、上海各法院就公司住所地认定的倾向性裁决 从近年来的司法实践来看,就公司住所地的认定,上海法院似乎形成了较为直接和穿透的裁决路径,从而倾向于将公司注册地直接认定为公司主要经营地,越过传统的三轮核查,笔者试整理此类案例如下: 1. 徐汇院在(2024)沪0104民初22504号裁定中认为,法人的住所地具有登记公示效力,不能将法人实际办公地点、生产经营地、销售地点、联系地点等法人的场所与之混淆。法人登记注册地址为确认法人住所最有效的证据,系处理管辖争议的依据。 2. 长宁院在(2024)沪0105民初9792号裁定中认为,公司应当遵循《民法典》的规定,将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登记为住所,故应当以公司工商登记的注册地确定管辖。 3. 闵行院在(2023)沪0112民初18612号裁定中认为,系争合同披露的地址记载为“地址”,并非记载为“住所地”,不足以证明公司住所地。根据《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十一条,市场主体只能登记一个住所或者主要经营场所。根据法律规定,法人的注册地或者登记地为住所地。 4. 虹口院在(2023)沪0109民初11928号裁定中认为,虽案涉三份合同载公司地址,但与公司注册登记地不同,注册登记证明是认定公司住所地的有效证据。 5. 静安院在(2023)沪0106民初19226号裁定中认为,法人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机关登记注册的住所地(即注册地)应为其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具有向社会公众公示的效力。虽然法人根据实际情况可以在异地经营,但不能因此否定注册地的公示效力。因此,在被诉法人的注册地与实际营业地不一致的情况下,原告选择向被诉法人注册地所在的法院提起诉讼并无不当。 6. 上海一中院在(2023)沪01民辖229号裁定中认为,依法需要办理法人登记,应当将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登记为住所,因此法人的住所地具有登记公示效力,不能将法人实际办公地点、生产经营地、销售地点、联系地点等法人的场所与之混淆。法人登记注册地址为确认法人住所最有效的证据,系处理管辖争议的依据。 7. 上海二中院在(2024)沪02民辖终884号裁定中认为,法人登记具有公示公信力,法人依法登记后,又以其登记的住所与其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不一致为由,提出管辖异议,不予支持。 8. 上海高院在(2022)沪民辖220号裁定中认为,公司法人应当将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登记为住所,法人住所具有特定法律含义且具有唯一性,不能将法人实际办公地点、联系地点等法人的场所与之混淆。注册登记证明是认定公司住所地的有效证据,当事人主张公司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与注册登记的住所地不一致的,应提供其在工商、税务等部门官方登记的材料予以证明。 仅就以上案例总结而言,尽管上海法院对于公司住所地认定的理由各不完全相同,但可以看出其均倾向于认为,鉴于公司法人存在将主要办事机构登记为住所地的义务,故法院宜推定公司注册地即为注所地,其公示效力优于合同载明地址、实际办公地点、生产经营地、销售地点、联系地等等。 5、上海本地法院就被告住所地认定实践趋于统一 据笔者了解,就上海法院公司住所地认定中的这一趋同现象,对于立案庭的立案工作亦可能有统一指引的效果。上海金融院在(2021)沪74民辖19号裁定中提及,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印发《立案问题解答(二)》的通知(沪高法立[2017]5号),全市法院在立案、管辖等程序中,认定法人住所地的执法口径应当统一到法人登记注册地址,即将法人登记注册地址作为确认法人住所最有效的证据,进而作为立案及处理管辖争议的依据。 同时,某区法院就网上立案申请回复“自2023年起,注册地不看合同披露的地址,也不看实际经营地址,而是看注册地。”此回复也印证了上海本地法院立案工作在该问题上可能存在统一的指引,或偏向趋同的态度。 6、两地不一致情形下对管辖预期的救济 尽管注册地和经营地法院管辖的效果需要视案件的实际情况而定,孰优孰劣并不能一概而论,但鉴于法律规定中对于被告实际经营地的强调,在商事活动中,往往参与者对于最终案件由被告实际经营地法院有较为合理的预期,其商业活动的展开亦可能基于此种预判。因此,虽然存在案件管辖稳定性的需求,但是如一律倾向于认定公司注册地即是被告住所地,有因噎废食的嫌疑,势必导致当事人商业目的及对法律预期落空的风险。从另一方面,当事人和律师也需要充分关注在现有司法实践中此类管辖问题的裁判倾向,在制定诉讼策略时做明智判断。 所幸的是,虽然上海法院确实存在较多案件倾向于认可公司住所地即为公司注册地的观点,但并非毫无例外。部分案件中,在查明被告注册地无办公场所及办公人员、无法收寄材料的情况下,上海本地法院查明公司办公场所所在地,进而认定该办公场所为公司住所地。另一些案件,法院根据交易的实际情况,以双方合同约定的公司联系地认定为公司住所地。故在上海本地法院推进此类注册地和实际经营地相关的管辖权争议时,仍可以尝试就公司住所地的认定提出异议,围绕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进行举证和争取。 不过,在法律实践中,永远是“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与其亡羊补牢,不如预防在前。笔者建议交易双方在签署协议时,如需要削减由管辖问题带来的不确定性,则在选择争议时可尽可能明确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并列明其为管辖法院,而非仅仅笼统的明确在哪一方公司所在地管辖。譬如在协议中,可以明确协议签署地为某地,约定管辖为签署地有管辖权的法院,将管辖权争议扼杀在摇篮中。实践中,部分法院对于管辖明显无争议的情况下当事人提出的管辖权异议,可能会认定为系当事人滥用诉权而予以惩戒,故明确管辖也可在争议发生时尽可能避免管辖权异议一审、二审导致的审理时间拖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