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微信,扫一扫二维码
订阅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打开手机,扫一扫二维码
即可通过手机访问网站并分享给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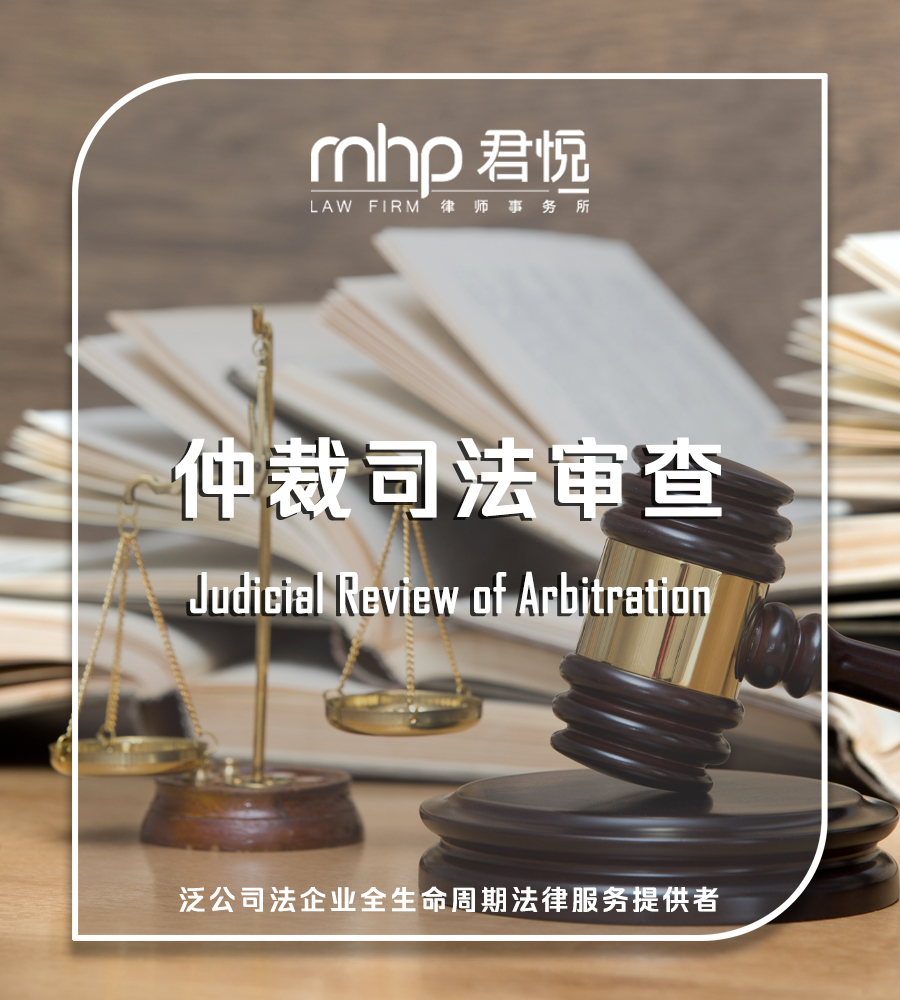
我国现行《仲裁法》第五十八条(以下简称“五十八条”)规定了可以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情形,以此建立了仲裁司法审查制度,当前对仲裁的司法审查主要面向仲裁协议、仲裁裁决两个维度。实践中,对仲裁裁决的司法审查多围绕程序问题和仲裁协议,而事实上随着仲裁的规范化运作,目前已不太可能在这两类问题上发生差错,故实践中撤销仲裁裁决的成功案例鲜有发生。
2024年初,笔者代理的一起某钢铁贸易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后引出的重新仲裁案件,最终仲裁庭全面纠正了首次仲裁裁决,君悦所通过本次有效代理为当事人挽回了500余万元的直接经济损失。透析本案实例,笔者想对仲裁司法审查制度做一定的实践分享和思考。
1、以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五项“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为由提起仲裁,可增加实体审查的可能性。
本案中,我方当事人系一上游钢铁贸易公司,根据合同约定,向某实业公司出售一批钢材,买家全程指示某中间人完成交易并支付了全部货款,后买家又在中间人协调下将货物转卖给第三方。此后第三方未能支付全部货款,而该中间人又因涉嫌贪污和合同诈骗被追究刑事责任,买方遂以上游钢铁贸易公司未完成交货为由提起仲裁,要求全额退款。首次仲裁的审理中,鉴于我方当事人无法获得和提供对方转卖货物的相关证据材料,又仲裁庭不认为有必要主动收集证据,故首次仲裁裁决要求上游钢铁贸易公司全额退回货款人民币500余万元。此后,笔者接受委托,以买家在仲裁庭审中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为由提起撤销仲裁裁决申请,要求重新仲裁,并同步向法院申请调查取证。经多番周折最终取得了买方与第三方之间的货物转卖合同、发票等材料以及中间人的口述笔录,而后法院在审查中认定买方在仲裁庭审理阶段未提供其直接掌握的货物转卖证据,而该证据足以影响本案事实认定,遂通知仲裁委重新仲裁。仲裁委经重新开庭审理,最终采纳我方意见,驳回了对方的仲裁请求。
回顾案件过程,以“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为由提起仲裁,法院审查重点包括:1、该证据是否属于认定案件基本事实的主要证据;2、该证据是否仅为对方当事人掌握,但未向仲裁庭提交;3、仲裁过程中知悉存在该证据,且已明确要求对方当事人出示或者请求仲裁庭责令其提交,但对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未予出示或者提交。
笔者提醒,对于己方无法掌握或可能存在的影响案件认定之证据,在仲裁庭审理阶段均应明确要求对方出示或提交,否则即便对方隐瞒也可能不纳入司法审查之列。
2、撤裁申请的同时,同步要求重新仲裁,可提高法院“发回”仲裁的可能性。
为了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仲裁司法审查的适用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仲裁司法审查案件报核问题的有关规定》(以下简称“《报核规定》”),明确要求下级人民法院拟裁定撤销仲裁裁决的,须向辖区内高级人民法院报核,且向最高人民法院报备;其中,涉外涉港澳台的撤裁案件、以“违背社会公共利益”作为撤裁事由的案件,必须逐级上报至最高人民法院,以此监督下级人民法院对仲裁裁决的司法审查。故实践中,如果仲裁案件确有疑点,法院撤销仲裁裁决的程序规定实质上存在三审机制,时间周期长,难度可想而知。若撤裁申请的同时,同步要求重新仲裁,则法院可以通知仲裁庭在一定期限内重新仲裁,并裁定中止撤销程序,也给了仲裁庭自我纠错的机会。相信如果存在确实足以影响案件事实认定和公正裁决的新证据,仲裁庭会作出公正处理。笔者代理的案件即是其中成功案例之一。
3、仲裁司法审查机制的改革方向
司法部于2021年公布了《仲裁法(修订)(征求意见稿)》,其中第77条对现行《仲裁法》五十八条第四项“伪造证据”、第五项“隐瞒证据”的撤裁事由规定进行了整合和限缩,将“伪造证据”事由拓展为“因欺诈行为取得裁决”,并删除了“隐瞒证据”事由,本意是限制法院对仲裁实体问题的介入,笔者对此持不同意见。
当前实践中,由于仲裁庭系临时组成,仲裁委不具有专业调查执法权,也不具备向律师开具调查令的权利,导致仲裁实践中当事人的调查取证权难以有效保障,一旦一方当事人刻意隐瞒一些掌握范围极小或者只有一方掌握的重要证据,对方当事人是很难取证的,甚至连尝试取证的可能都没有,如此必然影响对案件进行充分的实体审查,不利于体现仲裁的公正性。
虽2023年12月份,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推出了《关于开具调查令协助仲裁调查取证的办法(试行)》,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也办理了全国范围内首例法院依仲裁机构申请开具调查令的案件,但调查令申请和持有人系仲裁机构,实践中仲裁机构调查取证的频率和积极性显然有限,该制度如何保障仲裁过程中的当事人调查取证权利还需进一步的实践证明。故在此情况下直接限缩仲裁司法审查事由值得商榷。
笔者相信,《仲裁法》修订会充分考量实践做法和改革形势,保障司法公正和权威,也提醒大家注意仲裁制度的改革变化,确实维护本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