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微信,扫一扫二维码
订阅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打开手机,扫一扫二维码
即可通过手机访问网站并分享给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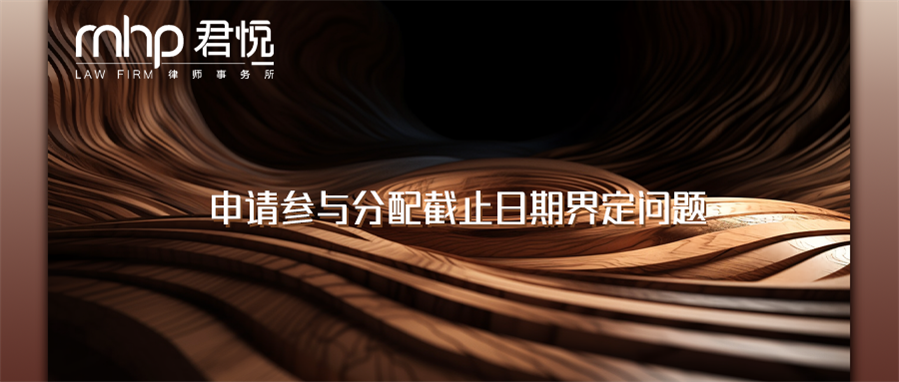
申请参与分配是执行制度中一项重要的内容,事关债权人实现诉讼目的以及合法利益保障程度的问题,也是体现人民法院司法权威的具体表现。然而,司法实践中,现行的参与分配制度存在着法律规定抽象化、分配标准不统一等问题,其中,关于申请参与分配截止日期的界定问题成为分配矛盾突出和影响执行效率的主要问题。笔者在此就这一问题作个初探,谈一下自己粗浅的看法,以供参阅。
参与分配制度的法律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五百零九条第二款规定:“参与分配申请应当在执行程序开始后,被执行人财产执行终结前提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执行规定》)第九十条规定:“被执行人为公民或其他组织,在被执行人的财产被执行完毕前,对该被执行人已经取得金钱执行依据的其他债权人可以申请对该被执行人的财产参与分配。”由此可见,法律规定申请参与分配的条件为以下几点:
1、被执行人是公民或其他组织(企业法人不在此列);
2、债权人必须取得对该被执行人金钱债权的执行依据(非金钱债权,比如行为执行,不在此列);
3、被执行人已由人民法院任一案件立案执行,进入执行程序,并且其财产已由执行法院采取执行处置措施(包括拍卖、变卖、以物抵债等,以相关执行裁定书有效送达为准);
4、申请参与分配的截止时间为被执行人财产被执行完毕前(被执行人财产执行终结前应理解为同一意思),也就是指被执行人财产已由人民法院处置完毕。
关于“被执行人财产被执行完毕”时间节点的争议
由于法律规定本身的抽象性和执行标准的缺乏,实践中各地人民法院对于被执行人财产被执行完毕,也即申请参与分配的截止时间节点存在着较大的不统一,从而引发分配异议救济程序的大量产生,严重影响了被执行人财产的及时分配,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债权人的损失。
主要观点包括以下几种:
观点一:以分配方案送达最后一个当事人为节点。
观点二:以执行款项审核通过发放日为节点。
观点三:以涉案财产所有权转移为节点。
笔者以为,观点一和观点二都无法避免一个问题,即时间段不确定性带来的财产分配时间无法截止。由于分配方案的送达涉及各个债权人和被执行人,有效送达时间无法高度统一,并且在送达过程中无法排除新的债权人的产生和新的财产分配申请的提交,因此,观点一的这个节点很难固化确定,始终会处于一个可变状态,从而导致分配方案也会始终处于可变状态中,费时费力。观点二存在同样的问题,执行款项的发放审核是以分配方案确定为前提,并且审批流程本身也存在一定的时间滞后性,况且审批时间的长短源于各个法院内部流程的不同,无法作出同一性规定,同样会带来参与分配截止时间的不确定性,从而无法固化参与分配的截止时间。如果以此来界定申请财产分配的时间节点,明显对当事人有失公允。
相对而言,观点三看似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也即涉案财产所有权从被执行人转移到了受让人名下,财产转移所得价款的性质转变为执行待分配财产,具备了执行分配条件,并以此为申请财产分配截止的时间节点。但是财产所有权通过执行处置发生的转移,只是属于一种财产表现形式的变化,法律规定的原则是执行法院向受让人送达了财产所有权转移的法律文书即告财产所有权转移完成,但是基于财产属性的去区别,比如银行存款、有价证券等动产的扣划、平仓提取等执行行为则一般不具备上述形式要件,因此仍不能排除在此节点之后相关债权人申请参与分配的请求。
申请参与分配截止时间的标准建议及理由
笔者认为,司法实践中一直没有很好地解决申请参与分配截止时间这个问题,是源于在财产处置和财产分配之间缺乏一个合法、合理并且相对固化的时间切割点,从而在法官自已裁量权的作用下导致了执行标准的不统一。从结果上看,无论是从执行效率角度还是从延伸的执行异议救济程序增量导致的司法成本提高的角度看,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都不尽理想。因此,结合过往的执行实践经验以及对相关法律规定从立法本意上的深度理解,笔者建议,申请参与分配的截止时间标准应确定为“涉案财产经执行处置后的确权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有效送达协助义务人之日”,理由如下:
理论依据:
无论是《民诉法司法解释》规定的“执行终结”还是《执行规定》规定的“被执行人财产被执行完毕”,这两种表述的本意均应理解为对被执行人财产整个处置程序的结束。这种“结束”的含义包括在财产受让人付清价款的基础上,人民法院向相关协助义务人有效送达该财产所有权转移的法律文书。也就是一旦人民法院完成向协助义务人送达法律文书,即表示相关财产处置行为和结果已经得到司法确认,整个财产执行已终结或者是被执行人涉案财产已被执行完毕,之后发生的完税、过户、做账等行为都只是协助义务人与受让人或执行法院之间的关系,与申请参与分配的债权人本身无涉。
实践作用:
人民法院向协助义务人有效送达法律文书的标准是有法律严格规定的,送达方式本身不存在争议。据此,送达时间比较易于确认,不会因为不同的案情产生不同的标准。这种时间节点的固化,有利于执行法院掌握财产分配节点,对于推动债权人及时、主动地申请参与分配具有积极的意义,同时也减少了针对申请参与分配截止时间的分配异议的数量,一定程度上节约了司法成本,既缓解了矛盾,也提高了执行效率。
实践支持:
众所周知,关于司法拍卖中债权人执行标的计算截止时间节点曾经是执行界争议多年的问题,理论上出现过“以申请执行之日为准”、“以裁判生效之日为准”、“以被执行人财产拍卖价款付清之日为准”、“以执行法院向买受人送达涉案财产所有权变更的法律文书之日为准”、“以执行款项发放之日为准”等多种意见。上海法院也曾面临这样的问题,并因此在上海高院的牵头下进行了广泛的研判。以上这些意见所列出的时间节点分涉执行程序中的各个节点,但都存在其不合理性、执行法院主观司法行为不确定性以及执行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度扩张的不利因素,从而被排除。最后确定的司法拍卖中债权人执行标的计算的截止时间为“拍卖成交确认书签订之日”,虽然这个时间点上买受人尚未付清全部价款,但是基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等司法解释已经对于“悔拍行为”有了明确的约束,因此可以把这种例外情况排除在外。这一标准上海法院沿用至今,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司法拍卖中债权人标的计算截止时间节点”的界定,给予了“申请参与分配截止时间节点界定”很好的实践性经验支持。因此,笔者认为,总结以往经验,实现“申请参与分配截止时间节点的统一性标准”是可行也可为的。
总 结
“申请参与分配截止时间的界定”无论从执行理论还是实务角度都是一个需要尽快解决统一性问题的课题,“以涉案财产经执行处置后的确权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有效送达协助义务人之日为申请参与分配的截止日”只是笔者的一个建议,希望据此可以推动司法实践中对此问题的重视和尽早解决,此为笔者撰写本文的目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