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微信,扫一扫二维码
订阅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打开手机,扫一扫二维码
即可通过手机访问网站并分享给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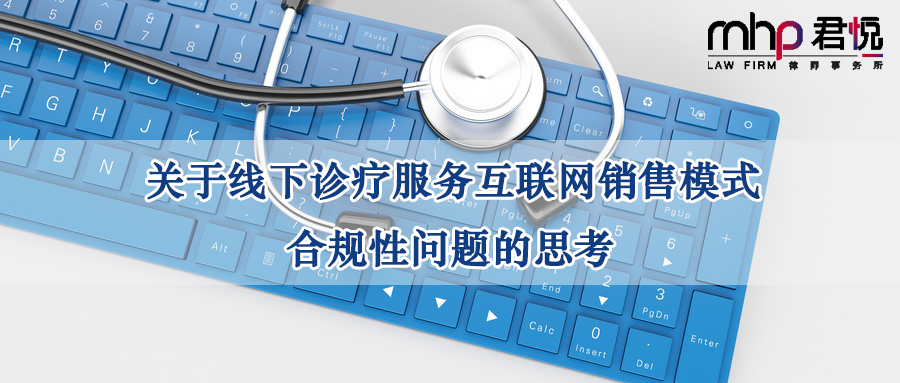
如果你在某宝搜索“体检”,可以找到由各种体检机构发布的琳琅满目体检服务套餐。如果你搜索特定的品牌名称,还可以找到牙科诊所、眼科医院、美容医院等各种民营医疗机构开设的天猫店。这些天猫店铺内既销售化妆品、医疗器械,也销售特定医疗服务套餐的电子券和在医疗机构线下消费时通用的抵扣券。我们在感叹某宝果然万能的同时,不禁担忧莆田系医院是否已由度娘转战某宝。目前的法律和行政监管真的允许医疗机构在线销售专业服务吗?
一、什么是诊疗服务产品
要研究医疗机构在某宝上销售这些产品是否合规,我们首先要明白这些产品在法律上的定义和归类。
这些产品的共同特点是它们都是由医疗机构所提供的服务。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习惯使用医疗服务这样一个词语,一些法律和政策文件中也用了这个词汇。不过更为专业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中对医疗机构所提供的服务使用了诊疗活动和医疗美容两个专门术语。根据法律条文的定义,诊疗活动是指通过各种检查,使用药物、器械及手术等方法,对疾病作出判断和消除疾病、缓解病情、减轻痛苦、改善功能、延长生命、帮助患者恢复健康的活动。医疗美容具体指使用药物以及手术、物理和其他损伤性或者侵入性手段进行的美容。虽然还没有法律文件对医疗服务与诊疗活动及医疗美容的关系进行严格的定义,但一般认为医疗服务包括了诊疗活动、医疗美容、以及两者之外的其他由医疗机构实际提供的服务。根据法律规定,诊疗活动和医疗美容必须由取得资质的医疗机构进行。虽然医疗美容服务由专门的《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予以规定,但很多基础问题上医疗美容与诊疗活动适用相同的法律,因此在法律讨论时我们可以把医疗美容理解为诊疗活动的一种,不过这样的分类在医学角度并不严谨。至于这两者之外的其它医疗服务,比如健康咨询、学术研究、住宿疗养等等,非医疗机构也完全可以经营。而文章开头我们所说的这些服务,都是必须由医疗机构才能提供。综上,我们暂且将这些服务统一称为诊疗服务。
健康体检服务是不是诊疗服务?
因为近年来健康体检服务的商业化程度很高,国内多家健康服务品牌企业先后挂牌上市,品牌连锁经营的健康体检服务网点分布广泛,导致很多人对健康体检服务机构的经营资质产生了误解。实际上健康体检服务也是诊疗服务的一种,属于疾病诊断活动,即诊疗中的“诊”。
提供健康体检服务的机构必须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具体的服务必须由执业医师和护士完成。卫生部曾在2009年专门出台了《健康体检管理暂行规定》就该问题进行明确,而且从规定的内容来看,开设一家健康体检服务中心的软硬件要求比开设一家普通的诊所要高出许多。
二、诊疗服务的线上销售与在线诊疗的区别
近期各地卫生行政部门陆续批准了一批互联网医院和互联网诊疗项目。这一现象有疫情防控背景的催生作用,但并不是突破法律监管的特事特办。
诊疗活动是一项高专业要求和高风险的活动,如果不作严格的行政监管,很可能给公共健康卫生带来隐患。因此除了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外(例如紧急情况下的无偿抢救、外出体检),医疗机构及其执业医师、护士的诊疗活动都必须在执业许可登记的实体场所内实施。其实早在2018年,国家层面就出台了鼓励开展“互联网+医疗健康”的产业政策导向。为了给医生通过互联网通讯方式进行远程诊疗活动作法律上的松绑,卫生行政部门在当年同时出台《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试行)》、《互联网医院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及技术规范文件。不过诊疗活动毕竟受到医学技术手段的客观限制,因此在线诊疗目前只适用于医疗机构对部分常见病和慢性病的复诊,以及患者在实体医院就诊时由接诊医生邀请其他医生通过互联网通讯方式参与会诊及出具诊断。
而我们所讨论的在线销售的诊疗服务,依旧需要由医疗机构在其线下的实体场所内完成,和通过互联网方式完成诊疗服务的在线诊疗并不是一回事。
三、诊疗服务的线上销售与线上挂号预约的区别
诊疗服务的线上销售与医疗机构或其他机构开展的线上挂号预约服务更为相近,不过两者之间还是存在医学范畴上的差别。
如果将诊疗服务的交易过程进行法律上的解构,我们可以大致划分出缔约与履约两个阶段。缔约阶段是患者和医疗机构就购买和提供某项诊疗服务达成合同的活动;履约阶段指医疗机构根据达成的约定向患者实施诊疗服务,以及患者向医疗机构支付诊金的活动。不过根据日常经验,在公立医院的门诊过程中,支付诊金有时是合同达成的标志,因此也会归属于缔约阶段。
我们在一次就医的过程中会依次达成不同诊疗服务合同,诊疗活动有时开始于缔约之后,有时开始于缔约过程中。举例来说:
当患者因感冒发烧前往医院就医时,完成挂号仅仅是双方进行的第一次缔约,患者购买的是医疗机构提供的首诊服务。
医生初步观察症状之后,一般会建议患者做进一步的血液指标检测,如果患者同意进行检测(具体标志为患者根据医生开具的检验项目付费单通过付费窗口或电子自助系统完成确认及付费),这时完成了一次新的缔约,缔约的内容是由患者购买医院提供的血液指标检测服务。
在疾病诊断结论形成之后,医生可能会建议患者接受口服药物、注射药物或回家休息等不同的治疗方案,如果患者选择了注射药物,相当于又缔结了新的诊疗服务合同。
在上述场景中,接诊医生建议患者接受某项检测和接受某种治疗方案的行为都是一种参与缔约行为(具体是一种要约行为),而这种缔约行为本身也是一种诊疗活动,必需要遵守相应的法律及诊疗技术规范。简单的来说,除了单纯的预约挂号之外,患者必须在得到医生的专业判断和建议之后,再对是否接受以及接受何种诊疗服务进行选择。如果盲目地允许患者自由选择诊疗服务,会产生医疗事故、过度医疗以及医疗资源分配失衡等医学伦理和公共卫生管理问题。因此,诊疗服务的线上销售与一般的线上挂号预约在医学监管要求上宽严有别。
我国已出台了相关法律对药品及医疗器械的线上销售及通过第三方交易平台销售的行为进行了规范,明确规定了参与方所需的经营资质。而目前对于在线挂号预约和诊疗服务的线上销售都没有出台具体的规定。
对于诊疗服务线上销售的问题,如果找不到对应的法律依据,我个人更倾向于认为这种模式不为法律所允许而非不为法律所禁止。
我们不妨做这样一种思考:如果允许医疗机构将任何诊疗服务商品化为服务套餐供消费者在互联网上自由选择,这显然违背了现行公共卫生管理政策严格规范诊疗活动的要求。如果政策上有所放开,允许部分诊疗服务在线销售,那么普通的第三方交易平台显然不具备对诊疗服务进行分类识别的专业能力,政策就必须在禁止第三方交易平台的销售模式,或允许在有资质的第三方交易平台上进行交易两种模式之间作出选择。无论是药品还是医疗器械的第三方交易平台经营资质,都是依托于卫生行政部门对于药品和医疗器械线下销售活动长期以来形成的成熟管理经验。而诊疗服务本身不存在所谓的成熟线下经销资质,诊疗服务由第三方在医疗机构法定场所以外进行销售或销售推广的问题是个十分敏感的政策话题,一旦政策放开就会形成合法的“医托”市场。因此我认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政策开放非医疗机构以第三方交易平台的身份参与诊疗服务的线上销售是不太现实的。
对于已经进入诊疗服务线上销售市场的医疗机构(几乎全是民营医疗机构)、纯粹的销售方和第三方交易平台来说,目前的经营模式蕴含着比较大的合规风险。
健康体检套餐的在线销售问题:
健康体检在诊疗服务线上销售中是规模最大的一个品类。根据相关上市公司的公开资料,健康体检服务事实上是有自建的销售团队和第三方的销售公司在从事体检服务的医疗机构法定场所之外进行产品推广的。早期这些销售活动针对的对象主要企业客户,根据几年前的统计数据,健康体检市场中个人客户占整体销售的比例不到20%。相关健康体检服务企业,早年利用特许经营体系和单用途预付卡发行制度将诊疗服务收费包装成像体检卡、体检券这样的一般商品向企业进行销售。之后为了促进零售规模的增长,发卡方又和传统的超商渠道开展战略合作。以上这些尝试从结果来看没有受到监管部门的公开质疑。随着在线零售整体规模的增长,近年来,体检服务零售经营也很自然地从实体渠道转向线上。
因为没有明确的文件和相关公开的表态,我们尚并不清楚监管部门对于健康体检服务线上销售持开放态度的具体理由和政策考量。不过这样一种现状肯定会吸引其他民营医疗机构的模仿。其他领域的民营医疗机构很自然地会思考,同样的销售模式,健康体检可以采用,不孕不育和整容塑形为何不能采用。于是乎,某宝上现在也开始出现民营医院销售终止妊娠术前检查套餐等比较令人咋舌的诊疗服务产品。
四、诊疗服务在线销售的医疗广告合规问题
如果说因为缺少法律规定导致部分医疗服务的在线销售成功了暗度陈仓,那么有法律明确规定的医疗广告审查本应当是诊疗服务在线销售过程中一个更加无法回避的合规性问题。
根据《广告法》和《医疗广告管理办法》的规定,任何以推销医疗服务为目的而对医疗机构或医疗服务所作的宣传,都可能构成医疗广告。诊疗服务在线销售过程中的产品展示方式实质上就是一种医疗广告。
按照现行的医疗广告行政管理要求,医疗广告只能由医疗机构进行发布。广告内容仅限《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载明的信息(名称、地址、诊疗科目、所有制形式、床位数)以及接收时间和联系电话,即所谓的白名单制度。
法律又在白名单的基础上进一步明文禁止具体的疾病名称、诊疗方法、诊疗药物、治愈率等涉及服务质量的信息出现在医疗广告之中,即所谓的黑名单制度。
通俗点讲,医院如果要做广告,按照现行的医疗广告审查标准,只能告诉患者我叫啥、我有点啥科室、我是民营还是公立的、我在哪、你几点可以来;至于我能看啥病、看的好不好都不能在广告中出现。
除了内容上的严格要求,医疗广告的审查程序也十分的严格。医疗广告的样张和发布方式需要事先递交卫生行政部门进行医疗广告审查,审查通过之后要在广告发布时标注医疗广告审查文号。
在如此严格的监管要求之下,我们依旧看到大部分线上销售的诊疗服务在网页中都没有标注医疗广告的审查文号,页面中各种法律禁止出现的信息也比较常见。这已是互联网医疗广告监管的老大难问题,这种困境或许与医疗广告由卫生行政部门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双重监管的制度安排有关。
医疗广告审查制度最早确定于1993年,由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医疗广告发布前的审查,由卫生行政部门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分别依据《医疗广告管理办法》和《广告法》及《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医疗广告违法行为进行查处。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查找1987年的《广告管理条例》并和现行的《广告法》作一下对比,会发现《医疗广告管理办法》一些制度安排的逻辑起点,也能体会到一些现在看似不合理的情况为何当时会被立法者所采纳。
现实中,由于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整个广告行业的管理从事前监管向事后监管进行转变,导致卫生行政部门猛然发现自己需要独自承担医疗广告事前审查的工作。由于可以构成医疗广告的医疗宣传行为数量太多,而公立医院也有刚性的宣传需求,为了减轻工作压力,卫生行政部门陆续将一些“刚需”排除在医疗广告审查范围之外。2006年《医疗广告管理办法》修订时将医疗机构在其场所内标示机构名称的行为明确列为无须医疗广告审查的医疗广告行为。2008年卫生部又在答复云南省卫生厅的内部文件中将医疗机构在门诊病历册、内部期刊及官方网站中刊载的宣传内容“暂不纳入医疗广告审查范围”。
另一厢,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2015年《广告法》修改之后拟对《医疗广告管理办法》一并进行修改并公布了征求意见稿,其中最大的变化在于废止医疗广告内容审查的白名单制度,全面改为黑名单制度,但事前的审查职责依旧由卫生行政部门承担。该征求意见稿至今未完成法律修订程序。
通过以上两部门对待如何医疗广告审查制度的想法,我们可以一窥两者彼此之间对于职责划分的态度。有莆田系医院搜索竞价排名、网络医托等问题在前,第三方交易平台上的医疗广告违规问题屡见不鲜也并不令人奇怪。
五、结语
互联网技术给公共卫生管理带来了便利,满足了医疗服务的消费需求,“互联网+医疗健康”产业拥有巨大的发展空间。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警惕“互联网+莆田系”的结合对医疗服务市场和公共卫生健康带来的破坏。诊疗服务在线销售的销售模式合规性问题和医疗广告合规性问题在实务中仍有许多模糊不清的地带,有待执法者和政策的制定者作进一步的明确,从而达到规范市场的立法目的。